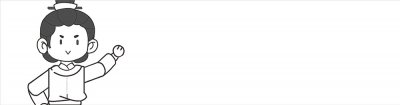迷失的乡镇
原创 | 王小民
《三国演义》卷首语云: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无数历史事实验证,这是一个普遍不争的真理,与人、与事、与物皆是。就拿我们身边的行政区划来讲,在这短短的不到二十年,大荔的乡镇经历一次次机构改革裁撤合并,从鼎盛期的33个、过渡期的26个到现在的17个,一路走来风景别致,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。


伴着新世纪钟声的洪亮敲响,拉开了又一轮区划调整的帷幕。大荔县的7个老牌镇(城关、许庄、朝邑、安仁、两宜、羌白、官池)先是在2000年中接纳了5个小伙伴,高明、双泉、冯村、下寨、韦林“脱乡升镇”,形成了21乡12镇的阵营。不过这一局面没有维持两年,2002年初便迎来了首次“缩水”,鲁安并入平民,雨林并入赵渡,乡还是那个“乡”;东七、婆合并入城关,汉村并入许庄,迪村并入韦林,华原并入范家,镇却非昔日“镇”,乡、镇各半(13乡13镇)就此形成。都说十年磨一剑,没用下十年世事可变了,2011年石槽并入官池、西寨并入韦林、八鱼并入羌白、张家并入下寨、步昌并入安仁、户家并入许庄、沙底伯士并入朝邑,传统阵营进一步做大做强,苏村、赵渡、平民、埝桥、段家撤乡立镇跃上“新台阶”,翻开了举县皆镇(18个)新篇章。伴随城镇化步伐的持续加快,冠名达半个世纪的城关镇于2015年易名为城关街道,两年后又一分为二,衍生出“东城”“西城”两个街道办。同时,镰山明珠高明并入两宜,河西新县平民并入赵渡,大荔县的行政版图以2办15镇定格,城关、东七、婆合、户家、汉村、伯士、沙底、步昌、华原、高明、八鱼、张家、西寨、石槽、鲁安、平民、雨林、迪村退出舞台渐成历史尘封。18个镇的迷失,“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”,从节约行政资源讲是有益的,从社会文化建设角度考量还真不好说!

大荔的历史源起西北,20万年前“大荔人”刀耕火种播撒人类文明,一条“母亲河”自镰山而河间斜插着曲流全境,串起了从“源”头段家经“中”心城关到“末”梢雨林完整的人类进化链,甜水沟旧石器时代遗址、沙底中石器时代沙苑文化遗址和婆合中石器时代埝头遗址,再到伯士赵家商代早期文化遗址,加上石槽苏胡西周遗址和沙底霸城战国遗迹,成体系地清晰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,就其多样性、连续性和丰富性而言,遍寻秦东、放眼三秦亦是无出其右的。如同有乡党坚称裁撤段家就是抹灭文明一样,试问洛河一线两岸哪个乡镇的历史不悠久、哪个没有大说道。大荔设州布县的历史逾三千年,有治必有城,史载东汉建安五年(200)移临晋县治与左冯翊郡治合为一所,形成了当时的超大型城市—冯翊古城,与此同时也便有了“城关”的概念。作为全县(大荔)、全州(同州)乃至全府(同州府)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城关自然是物汇人聚、云趋鹜赴之地,贵为“东府古都”。星星跟上月亮沾光,1400年前的唐贞观时期,有一个村子因位居冯翊古城西边七里而得名七里,随着不断地发展壮大,清道光年间“一分为四”,居东的村子有了“东七”的称呼,后来更是变成了乡政府所在地,从南北西三面拱卫城关将近四十年,现在老大荔人记忆深处的氮肥厂、乳品厂、棉浆纸厂等“老工业”底摊便在其境。城东的婆合与城西的东七“同日生、同日亡”,1964和2002上演了共有的“喜”与“悲”,不过和东七的“工业之刚”比起来,婆合更具备“文化之柔”。“婆合”名源中国二十四孝故事之《寿昌寻母》,北宋以来孝悌文化口传身授深入人心民意,优良的家风传承是婆合千年不衰的闪亮名片。比肩于婆合的孝道,伯士的礼贤下士亦是美誉,“平民省长”王双锡的朴实、敦厚、亲民劲至今口碑载道。

东南是天设地造的福地,这不仅存在于山岳相依、三河汇流的自然奇观,更因为这一方系着“大荔”的文化源头。史载公元前720年,原居甘肃东部的大荔戎族部落“灭同阝据芮”,在滨河处建“王城”立大荔戎国,自此“大荔”概念便成为最具生命力的官方称谓。其实还有早的,毗邻而居的“芮”就比它最少提前了三个多世纪,而且传承的是正统的商周文化。于是,这里便井喷式地精彩起来了,土著渔猎文化、戎族游牧文化、古芮农耕文化三者相融相生,绵延扩展到县域全境,而且是“文化”到“文明”的跨越式,从而牢牢奠定了大荔大力发展的基石。时至今日看大荔“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”,三农综合实力最强、发展潜力最大的,依然莫过于东南曾经的几个乡镇。鲁安、平民、雨林、迪村是清一色的移民乡镇,原本人老几辈世外桃源般安居着,失望大过期望的“三门峡水库工程”打破了原本的平静祥和,移民搬迁伤筋动骨劳民伤财,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十万人出去、八十年代中六七万人返迁,沿黄河、渭河便多了6个专意安置移民群众的乡。抛过目下仅存的赵渡不言,顺流散布在秦晋黄河大峡谷里的鲁安、平民、雨林,文化的根脉都相当绵长。据说有三板斧威力的唐鲁国公程咬金封地黄河滩,加之民国十八年(1929)闹年馑时山东流民迁居,“鲁”“鲁”的跨时空安居诞生了“鲁安”。新中国初属平民管、改革开放期仅支撑门面十四五年,新世纪初重归平民的怀抱也算逃不脱的“轮回”。其实平民也没好到哪里去!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查黄河滩地之争设立平民“一县跨两岸”,不想这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也来得太过频繁,县城不到十年便由黄河之东(今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西侧)后靠到西岸新址,接下来水患加人祸(抗战)频扰,美好的“平民政治”寓意勉强支撑到解放初便作古了。先是归到朝邑,没料到朝邑在58年也叫大荔收编了,后来倒算“因祸得福”,移民前连个乡都不是,返库重建后复立乡,新世纪以来扩域(鲁安)升格(乡为镇),那是一个“风光”。此风光非彼“风光”,真正的风光景致在雨林。坐拥黄河南滩的平和柔静,远眺华山如屏,近看烟树入画,最是激浪相荡“三河口”处处动魄、景景慑魂,足可比拟当年《朝邑十二景》之“渭川烟雨”情景:风袅杨柳,云接炊烟,村树帆樯,川原迷朦……胜似植被丰茂溪流涓涓的“雨林”生态。溯渭水而上的迪村亦有如此美妙,不同在于它更突显人文之美。靠沙(苑)面渭(河)的迪村本称遆村,先民是有着元明帝王血统的皇室贵族,他们文化才艺兼备,雅化“启蒙开导”而名迪村,雅致“启迪后昆”贤良辈出,“现代古琴第一人”张友鹤自是其中佼佼者。

大荔东北(铁镰)山在北、(黄)河在东,原崖壁立、梯田层叠的独有地貌呈现出别样地理优势。《大美大荔》言:旭日东升,照在黄河西岸横亘六十余里、高约百米的台原上,一片金黄、光灿夺目,这片广大的区域谓之“朝坂”,亦叫华原山。“华原山”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山”,诗情画意下它是唐代诗人王之涣“白日依山尽”的巍峨雄壮的“精神山”,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、范文澜力主的华夏民族“父亲山”。地理影响并决定文化,有山有水的“华原”风景虽美却也苦凋,河滚水滥几成梦魇,黎民百姓的创业艰辛与春和景明形成鲜明反差,欣喜民谣里“远眺像江南、近看似延安”的华原,今世已转身“渔湖镜天”“多彩渔村”乡村游,幻化出和谐文明幸福的风采。原下成了“灾”的水在原上的高明实实是缺货,这块最先享受阳光沐浴的厚重黄土居镰山之巅,守着“朝晖吐清气,悠然见南山”的奇景神韵,过着水比油贵的恓惶日子,硬是逼出了高明人的“高明”。耕读传家、接续发展的良好风气在这里得以完美诠释,就如同高石脆瓜的“香、脆、酥、甜、美”一样,高明人走到哪里干啥事都吃香,只是可惜“乡魂”随着并入两宜没了。高不成低不就的步昌“坐”在华原崖头,低头看华原、抬眼望高明,一脸的尴尬、满腔的不平,想起老先人“结草衔环”的仗义、平朝起义的悲壮,委屈到眼泪往肚子里流,多亏逢了个叫小坡的“好后生”,“步步昌盛”的衣钵才传承的更为美好。缠着镰山的乡镇有成十个,消亡最早的却是历史最久的汉村,西汉武帝凿渠而万卒落户,“十里烂汉村”挺过了比别地长久得多的苦难,临了没有避过败落,跟遍布境内的砖瓦厂一样每况愈下,结果难免令人唏嘘。跟沟子并入许庄的“难弟”叫户家,白菜芯的“好”谁都能看上,明代潼关卫屯兵营寨星罗棋布,“荔北战役”激战响彻东西大壕,巍巍丰碑高高树立,却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。

东北西南,张家华原。西南的沙窝窝有着别样的内陆沙漠景致,从东边的“赵(渡)头”到西边的“孝(义)尾”,沙底、西寨、石槽、八鱼、张家全在这个框框里。沙底的名号标明了沙海高梁下“宝窝窝”“菜窝窝”,一代战神吴起在此筑城守霸业、著述传后世,同朝皮影、碗碗腔宛转悠扬于麻子池上空,葱姜蒜和“水上漂”的莲花池辣子贡得了皇上也入得百姓的厨房。西寨的“寨”指西王寨,提及历史它虽是唐沙苑城中的一粒沙尘,在“缭以周墙百馀里,苑中騋牝三千匹,丰草青青寒不死”(杜甫《沙苑行》)的宏大里,地域光辉尽情散发,沙苑文化发祥地、沙苑沙苑城腹地、文人雅集“白楼”、秀丽俊美太白池……衬托出沙苑明珠的古朴雄浑美。某种意义上讲,石槽是吃了果子丢了名分的“憋屈主”,如同没挪窝的上门女婿承继着女方的名号。石槽有着与沙的众多故事,旗下的九龙泉传说是同州的名源,洛河岸边的桃花和隋文帝高筑的“看花台”更是载入史册的壮观,只可惜人硬不如事硬,在靠综合实力评判的时候还是汇入了官池的“汪洋大海”。要这么说,八鱼绝对服气,毕竟虽拥有“八女井”“八鱼李氏”“八鱼石墓群”等文化遗产,但跟荔西首镇羌白相较必定处下风,新中国以来两次三番的归属让谁都觉得再自然不过了。张家把着大荔的边边,隔河看华州贴脸接临渭,十里奓村一摆溜,十里沙洼水汪汪,南北莲池的莲藕、上下沙洼的打瓜以及遍布张下路、东张路夹角纵深的脆甜红枣,想想都不由得流口水,只不过物是人非、品牌换了。

物竞天择本为自然规律,社会变革也是老百姓拿不了钥匙主意的事。只可惜众多文化遗产风雨飘零下的迷失,更盼望尽可能多的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性保护,此为小民所愿,亦当是大众心声。(来源:美丽大荔(美篇))